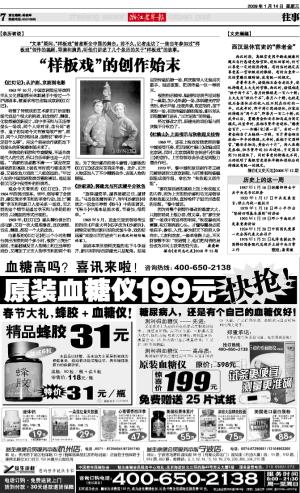|
 |
|
|
2009年1月14日 |
|
||
| “样板戏”的创作始末 |
| “文革”期间,“样板戏”曾垄断全中国的舞台。前不久,记者走访了一些当年参加过“样板戏”创作的编剧、导演和演员,听他们讲述了几个亲历的关于“样板戏”的故事。 《红灯记》:从沪剧、京剧到电影 1963年10月,中国京剧院总导演阿甲从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手中接过一个沪剧剧本,被要求将它改编成京剧《红灯记》。 唱惯了传统戏的艺术家们开始接触现代戏是个很大的挑战,唱念做打、舞美、化妆都要创新设计。戏中李玉和与王连举接头一场戏,两个人背对背,念台词“老李,鬼子的岗哨今天布置得很严密”,然后,两个人同时转回身,接着说“看样子一定有什么事”。用这个转身动作就把地下党接头的环境感体现出来了。 传统戏的唱腔和节奏缓慢,不适合演现代人的生活,所以音乐革新也是一大问题。“‘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就是在京剧唱腔的基础上吸收当时流行歌曲的节奏,又吸收地方戏的二八板创造的。”年过八旬的中国京剧院演员曹韵清说。他是原《红灯记》中侯宪补的扮演者。 观众今天看到的《红灯记》,并非1964年的演出版本。当年,领导看了会演后,建议突出李玉和的革命行动,加上“粥棚”李玉和和磨刀人接关系一场戏,而之前的这个情节是通过李玉和与李奶奶的对话,以倒叙的形式出现的。 1969年,《红灯记》要从舞台演出拍成电影,又有一次大规模修改,此次剧情、音乐、舞美,都有一个大的改动。 电影版的《红灯记》把三个小时的舞台演出压缩到两个多小时,根据“三突出”原则,主要删减反面人物鸠山和王连举的戏份,又增加了正面人物李玉和的两个唱段。为了突出激昂的战斗豪情,电影版的《红灯记》还改用交响乐伴奏。此外,正面人物还加入了不少舞蹈动作,表现人物的刚强。 《沙家浜》:郭建光与阿庆嫂平分秋色 “旋律越简单,越容易被记住,越普及。”马连良的嫡传弟子、当年《沙家浜》导演之一迟金生哼着《智斗》中的曲调说,“《智斗》中基本是流水板,节奏快,很简单。” 1969年9月,迟金生接到领导传达的指示:《芦荡火种》名字改为《沙家浜》,剧情应更突出新四军的武装斗争,戏的结尾要“直接正面打进去”(打进汉奸胡传魁的家)。 原剧本来围绕阿庆嫂的地下斗争展开,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只是配角。结尾是胡传魁结婚一场,阿庆嫂带人化装成吹鼓手,混进敌巢,把胡传魁一伙一举消灭。 根据指示精神,编剧和导演苦思冥想了一星期,加入《奔袭》一场,即郭建光疗好伤后,杀出芦荡,连夜奔袭,攻进胡府。接下来的一场,在胡传魁结婚的现场,新四军从后院翻墙打进去,“正面进攻”胡传魁。 经过修改之后,郭建光的戏份堪与阿庆嫂平分秋色了。 《杜鹃山》:上面指示与秋收起义挂钩 1969年,还在上海戏校做老师的黎中城接受任务,把话剧《杜鹃山》改编成同名京剧。同时,北京京剧院也在进行《杜鹃山》的创作。上面有领导表示:还是两股力量合作吧。 1970年,黎中城和原话剧作者王树元被借调到北京京剧院,与汪曾祺和杨毓珉组成创作组,命名为“秋收起义创作组”。 “要在原话剧的基础上加上秋收起义的内容,因为上面的指示要和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挂钩,宣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黎中城说。 因为对整个剧情作修改的难度太大,只能在唱词上想办法、做文章。在“家住安源”一场戏中有这样的唱词,“秋收暴动风雷骤,明灯照亮我心头。才懂得翻身必须枪在手,参军、入党,要为那天下的穷人争自由。工友和农友,一条革命路上走。不灭豺狼誓不休!”在剧情上,他们把柯香的身份改为井冈山派来的党代表。 柴爱新 摘自《老同志之友》2008年12期 |
|
收藏 打印 推荐 朗读 评论 更多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