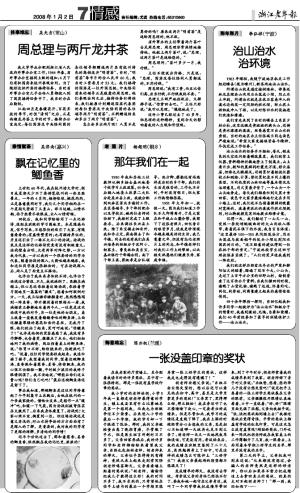1963年深秋,我随宁波地区机关工作组赴嵊县(现为嵊州)、新昌两地治山治水。
所谓治山就是通过植树造林、停垦还林及在深岙山沟用石头筑成小坝,阻止水土冲刷。所谓治水就是在泥石容易冲入的溪水边构筑一定间距的拦水坝,防止泥土淤积或冲入下游,以及对陈旧水利设施进行改造和修建。
我们首先来到了当时的嵊县上东区少柏公社,这里远眺是黄斑斑的瘌头山,近俯是黄水滚滚的溪流,丝毫感觉不出山水的秀丽。当时的地区办主任张瑞兰同志面色严峻地说:“希望大家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尽快完成工作任务。”
治山治水的任务并不轻松,每天,铅灰色的天空还闪烁着稀疏晨星,我们就背上仪器、资料精神抖擞地登上了制高点。山上看日出,朝阳的晨辉刹时霞光万道、彩云层层,但谁也无暇顾及。司测员忙着按放仪器校正和测绘、计算。登记员纪录不同土壤的类型、不同性质的山林田地等基本情况及治理意见。司尺员最辛苦了,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奔走。每天我们都要忙到天黑才肯回家,夜色中大家步履艰难地行走在乡间小路上。这时,我们还不忘借着微弱的晚霞对宽阔的、流着黄泥水的溪流作拦水坝规划,对山脚破损荒芜田地提出维修方案。
记得一次,我们翻过了一山又一山,突然一条陡峭蜿蜒曲折的大山沟跃入眼帘,看着泥石俱下的水流,我自言自语道:“这里最好100—150米间距筑谷方,用石头筑成与坡面相平的坎头小坝达到阻水固泥的目的。”这不经意的建议得到一位农林干部的肯定:“宁波林校学生这回可理论联系实践了。”人们的笑声使我感到一阵欢欣。
我们就这样历经雪压冬云的严寒和骄阳似火的酷暑,踏遍了近百个大、小山头,走过了上百平方公里的田野山村,绘制普查了达百余公斤资料。当我们撤回的时候,谢绝了山货礼物、谢绝了远送,怀着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建立起来的感情依依惜别。
四十余年弹指一挥间,当回忆起我和许多同学一起被评为“治山治水”积极分子的情景时,我感到激动、无愧、自豪和荣耀:我们40年前就参加了最早的环境保护工作——治山治水。